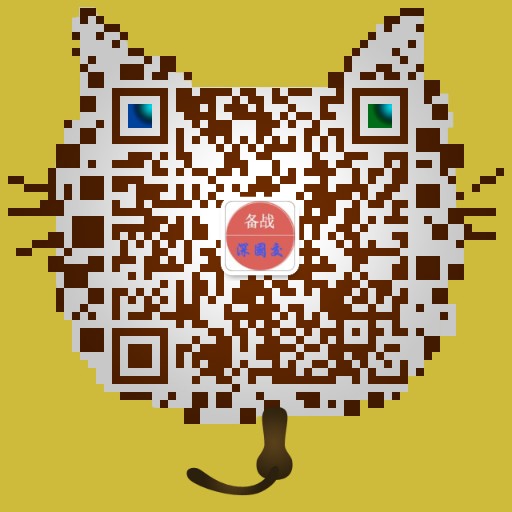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1965年,剑桥协会举办了一场辩论,由詹姆斯·鲍德温 (James Baldwin) 和威廉·F·巴克利·Jr (William F. Buckley Jr.) 就「美国梦是以美国黑人为代价实现的」这一议案展开辩论。两年前,鲍德温的文章《下一次的大火》已经发表;而巴克利是保守杂志《国家评论》的创始人兼总编辑,担任这一职务已有十年之久。两位男士都处于他们的名望巅峰,分别是美国民权运动和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
鲍德温首先发言,以一种沉静而顽抗的语调开始:「我发现自己不是第一次处于一种耶利米的位置。」[1]他要传达的是坏消息,但更像是历史而不是预言:
我非常严肃地声明,这并不夸张:我摘过棉花,我运到市场,我在别人的鞭笞下修筑了铁路,所有这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的。南方的寡头统治阶层,直到今天在华盛顿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都是由我的劳动和汗水、对我的妇女的侵犯以及对我的孩子的谋杀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在自由之地、勇敢之家。没有人可以质疑这一陈述。这是历史记录的事实。 巴克利并没有不同意,而是以一个实用主义的挑战来回应鲍德温:
实际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在美国应该尝试做些什么......来消除那些心理上的羞辱,我和鲍德温先生都认为这是歧视的最恶劣方面?......我同意你,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可耻的局面,但我要求你不要将政治当做一种直截了当的东西......[黑人] 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来强调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事实。他们已经为激发道德关切做了很多努力。但他们现在应该往何处去? 「直截了当地」[2]政治是一种坚持应该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政治,一种拒绝将目光从过去暴行转移的政治。正如鲍德温明确指出的,这也是一种愤怒的政治。相应地,巴克利鼓励一种务实的政治,一种将目光从过去的失败转向未来以实现次优结果的政治。无论其丑陋的历史如何,巴克利继续争辩说,美国梦现在是美国黑人的最大希望。除了在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社会美国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比这更能改善他的境况呢?还有哪种梦想比美国梦更值得追求呢?对过去不公正的苦涩坚持只会导致自我毁灭。黑人必须避免鲍德温所代表的「一种愤世嫉俗、一种绝望、一种偶像破坏主义」。因为最终,巴克利警告说,黑人的愤怒将会遭到白人的暴力回应:
如果最终发生了一场对抗,一场激烈的对抗……那么我们不仅将在剑桥协会战斗……我们将在海滩上、丘陵间、山脉中、登陆场上战斗。 宽容或许可以向黑人延伸,但他们的愤怒不能被容忍。暴怒的预言必须让位于冷静的务实主义。
巴克利坚持认为,黑人的愤怒是错误的,因为对黑人自身来说是适得其反的,这把他置于一个悠久的智识传统之中。虽然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认为适度的愤怒是男性美德的标志[3],但斯多葛派则主张完全消除愤怒,因为它必然产生的是更多的恶而不是善。因此,塞涅卡将愤怒描述为:
愤怒是所有情绪中最可怕、最狂乱的。其他情绪中都有一些平静与宁静的元素,而愤怒完全是暴力的,并且在愤恨的冲击中存在,带着一种最不人道的对武器、血液和惩罚的渴望,只要能伤害别人,就不顾自己的安危,扑向匕首的尖端,渴望复仇,即使可能会把复仇者自己也拖下水。[4] 早期基督教神学家约翰·卡西安建议我们「永远不应该……因为好的或坏的原因而生气」,因为愤怒威胁着用「阴影」使我们「心中的主导光芒」变暗。[5]最近,格伦·佩蒂格罗夫 (Glen Pettigrove) 主张应该避免愤怒,因为它倾向于污染我们的认知理性能力。[6]佩蒂格罗夫与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Nussbaum) 一起进一步主张,即在政治不公正的情况下,也应避免愤怒,因为它倾向于疏远潜在的盟友,加剧冲突,并最终破坏对公正结果的追求。[7]佩蒂格罗夫建议用温和的美德代替政治上的愤怒,而纽斯鲍姆则建议采取一种公民之爱的精神。[8]
这种对愤怒的「适得其反批评」也以具体的、政治化的形式出现,就像鲍德温和巴克利之间的辩论一样。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写道,马尔科姆·X (Malcolm X)「在表达黑人的绝望时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创造性的替代方案」,这对「他自己和我们的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为「在黑人贫民区进行暴怒的、煽动性的演讲只会带来悲伤」。[9]美国记者乔纳森·查特 (Jonathan Chait) 为奥巴马总统不愿公开表达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愤怒辩护,理由是奥巴马采取了鼓励黑人「专注于他们可以控制的事物」而不是「出手报复」的「明智做法」。[10]针对大陪审团未能起诉一名杀害一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少年的警官,密苏里州弗格森最近的骚乱也再次引发了许多自由派同情者呼吁理性和冷静。在以色列2014年的「保护边缘行动」中,以色列在被封锁的加沙地带杀害了大约1500名平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 (Nicholas Kristof) 在谈到这一事件时,敦促巴勒斯坦人放弃愤怒,因为愤怒「除了增加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外,什么也没有做到」;克里斯托夫认为,如果巴勒斯坦人能够采取甘地的模式,结果将「在世界各地产生共鸣,巴勒斯坦人将实现国家独立和自由」。[11]长期以来,女性被告诫如果她们在争取女权的过程中不那么激进,进展会更快。LGBT活动人士也被其盟友提醒,进步需要时间,而过于激进反而会阻碍进展。人们常常认为愤怒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被视为不应该愤怒的决定性理由。这种劝告往往是出于对不公正受害者至少表面上的同情,就像巴克利做的那样。

马尔科姆·X,美国民权运动家,以对暴力革命的推崇闻名
「适得其反批评」的对立面存在于一种主要植根于黑人和女权主义思想传统中,它挑战了「愤怒充其量只是自我伤害的武器」这一预设。在《愤怒的用途:女性对种族主义的回应》一文中,奥德丽·洛德 (Audre Lorde) 写道:
每个女性都有一个储备充足的愤怒武器库,这些武器可以有效对抗那些引发愤怒的个人和制度性的压迫。精准地聚焦愤怒,它可以成为推动进步和变革的强大能量源……将愤怒表达并转化为行动,为我们的愿景和未来服务,这是一种解放性和赋予力量的澄清行为。[12] 对洛德来说,女性的愤怒不仅是可以直接服务于政治目标的「能量源泉」,也是一种「澄清」的源泉,是女性更好地认识自己所受压迫的一种方式。包括玛丽莲·弗莱 (Marilyn Frye)、乌玛·纳拉扬 (Uma Narayan) 和艾莉森·贾格尔 (Alison Jaggar) 在内的几位女权主义哲学家,都追随洛德,强调了愤怒在认知上的积极作用。[13]丽莎·特斯曼 (Lisa Tessman) 认为,虽然受压迫者的愤怒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无法被视为美德——因为它缺乏实现幸福所需的适度——但在更偏向后果论的意义上,愤怒可以促进他人的幸福,从而依然具有美德。[14][15]这一反对传统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原因在于它提醒我们,适得其反批评通常基于可疑的经验假设。毕竟,认为如果没有马尔科姆·X愤怒的抗争,白人美国会愿意接受马丁·路德·金关于统一和后种族主义国家的愿景的这种想法在历史上是天真的。同样地,认为愤怒对那些自我观念被贬低和仇恨所塑造的人没有任何有益的心理可能性,这种想法或许也是天真的。[16]
话虽如此,对于愤怒的效能进行争论的批评者和支持者之间的辩论往往会掩盖愤怒的一些重要方面。在规范意义上,愤怒并不仅仅局限于其效果。对于任何一种事与愿违的愤怒,我们仍然可以问:它是否是对世界现状的恰当回应?即使愤怒并不产生实际成果,它是否仍然适当?一些哲学家如麦卡拉斯特·贝尔 (Macalaster Bell) 和艾格尼丝·卡拉德 (Agnes Callard),曾经辩护愤怒有时是对不公正世界的合适的回应。[17]总体而言,哲学上对愤怒的辩护往往是在与适得其反批评的辩证对立中塑造的,因此主要集中在愤怒的好处上。相比之下,我想先承认适得其反批评者关于愤怒通常使情况变得更糟的经验假设,从而聚焦于那些愤怒尽管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仍然恰当的情形。[18]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提出,审慎理由和恰当理由会分离,产生实质性的规范冲突。我将论证,随之而来的有两点。首先,适得其反批评者需要解释为什么在这种冲突中,审慎理由优先于恰当理由;在这一负担得到解决之前,不能显而易见地从愤怒的适得其反效果得出全面禁止愤怒的结论。[19]其次,这种冲突——受压迫者必须在适当地愤怒和审慎地行动之间做出选择——本身构成了一种未被承认的不正义,我称之为情感不正义。
我将按以下方式展开。在第二部分,我将阐述什么是适当的愤怒。在第三部分,我将描述由适当但有适得其反效果的愤怒引发的规范冲突的本质,这种冲突表现为在使世界变得理想与情感上认可世界现状之间进行的令人不快的选择。然后,我将解释为什么这对适得其反批评提出了挑战,并引入情感不公正的概念。在第四部分,我解释了适得其反批评者不能通过辩称其真正目标不是愤怒(无论是否适当)而是其刻板印象表达来回避我的挑战。第五部分,我总结讨论通过消除理性与愤怒之间的虚假二分法来缓解情感不公正的前景。

在政治语境中讨论愤怒的方式与我们在日常情况下谈论愤怒的方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普通对话中,我们确实会讨论愤怒是否是对现状的适当回应,现状是否提供了愤怒的理由,以及一个人的愤怒是否是对现状的恰当回应,而不考虑其效果。我想说,日常讨论时,好像愤怒存在于内在理由的范畴,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理由。假设你是我的朋友,我问你为什么对我生气。你回答:「因为你又迟到了!」我说:「你不应该生气。我告诉过你我会迟到。」我们谈话的主题是,你对我迟到的愤怒是否真正恰当,我的迟到是否确实构成你愤怒的一个内在理由。
在日常对话中,我们可以并且确实区分内在和工具性的愤怒理由。如果你是那种喜欢生气的人[20],我可能会对你说:「我知道生气让你感觉良好,但你实际上没有理由生气。」 在这里,我对比了你的生气的工具性理由——它让你感到愉悦——和你(缺乏的)生气的内在理由。令人惊讶的是,在日常的情况中,从内在到工具性的愤怒辩护的转变通常是(充其量)无关紧要甚至是(最糟糕)道德愚钝的。如果一个不忠实的爱人对你的愤怒说:「你不应该生气,因为这只会让我更多地背叛你」,那么你立即得到了愤怒的额外理由。因为现在发生了两件错误:首先是最初对你信任的背叛,其次是随后拒绝把你对这种背叛的愤怒看作是存在于内在理由空间中的。
适得其反批评的支持者有可能犯下第二种错误,这种错误类似于不忠实的爱人所犯的错误。这个错误在结构上——即使在意图上不完全相同——与最直接压制愤怒的表达方式有一些共同之处。厌女者通过称一个女人为「尖锐」或「刺耳」来贬低她的愤怒;种族主义者通过称一个黑人为「暴徒」或「动物」来贬低他的愤怒。这些不仅仅是侮辱,而是修辞策略,将愤怒的解释背景从理由的空间转移到原因的空间。厌女者或种族主义者把女性或黑人的愤怒解释为劣等性格的产物,把「为什么这个人生气?」这个问题的解释当作因果的而不是证成的。因此,偏见者会说:她生气只是因为她是个尖刻的泼妇;他生气只是因为他是个暴徒。因此,偏见者掩盖了女性或黑人愤怒是恰当的可能性。无论有意与否,适得其反批评者也达到了类似的效果。通过关注行动者愤怒的所谓负面效果,批评者再次将我们从内在理由的空间转移到工具性理由的空间,从而掩盖了行动者的愤怒是恰当的这一可能性。
那么,什么时候一个人的愤怒是恰当的呢?考虑愤怒与另一种消极情绪——失望——之间的区别。使愤怒作为愤怒可以被理解,并且与仅仅是失望不同的,是愤怒将其对象呈现为违反道德的:不仅是违反了人们希望事情发展的方式,而且是违反了事情本应如何的方式。[21]当我说我感到失望是因为你背叛了我时,我暗示我希望你没有这样做;相比之下,当我说我愤怒是因为你背叛了我时,我暗示你根本不应该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我因为你背叛了我而生气,我就必须相信你不应该背叛我;我在这里关心的是我的情绪所表达的规范性评价,这可能与我对情况的规范性信念不一致。)[22]由于愤怒将其对象呈现为涉及道德违反,因此只有当某事 (p) 构成真正的道德违反时,一个人对于p的愤怒才是恰当的。如果我因为你没有来参加派对而生气,但你不参加派对并不构成道德违反,那么我的愤怒很难说是恰当的。[23]
对于像努斯鲍姆 (Nussbaum) 等人常见的观点[24],即愤怒必然包含对冒犯方造成痛苦的愿望,和/或者相信冒犯方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如何看待呢?[25]努斯鲍姆和许多其他当代哲学家一样,继承了这一来自古代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似乎都认为愤怒本质上包含了对复仇的欲望,并且古代的故事(尤其是《伊利亚特》)表明,复仇冲动的满足确实回应了愤怒的欲动召唤。[26]反过来,努斯鲍姆利用这一观点支持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哪种情况,愤怒都从中产生了错误的信念,即复仇能够消除原始伤害,或者是对冒犯者进行道德上可疑的贬低的愿望。[27]也许这对古人来说是真的。但对我们来说呢?愤怒的本质——我们如何体验它,它召唤我们去做什么——可能会随着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例如,迈尔斯·伯内亚特(Myles Burnyeat) 认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荣誉行为准则的侵蚀导致了一种不涉及复仇的愤怒形式的普遍存在——这在古代哲学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28]的确,有人可能认为,没有复仇欲望的愤怒是我们许多人所熟悉的一种情感。[29]假设我的朋友背叛了我,我对她感到愤怒。我可能想要复仇。但我是否可能想要——我们是否都曾想要——朋友认识到她给我造成的痛苦,她对我所犯的错误?也许这种认知本身就会导致痛苦。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想要我的朋友受苦。但我并不希望她遭受无谓的痛苦;我的愤怒并不意在让她摔断腿或生病。相反,我希望她体验到那种正是我所经受的痛苦。如果这是愤怒的一种可能方式——我怀疑这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断言愤怒本质上涉及对复仇的欲望就是错误的。因为渴望被认可并不等同于渴望复仇。因此,我认为,对愤怒永远不恰当的最有力的论据——即愤怒必然涉及一种总是不恰当的复仇冲动——应该被搁置。

《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开篇
我的愤怒必须针对真正的规范违反,这是愤怒恰当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足够。还需要什么?我并不打算对恰当的愤怒进行完整的分析——对于我的目的来说,我也不需要——但我会提出一些简要的观察。我已经说过,对于S的愤怒,如果p是恰当的,那么p必须涉及到真正的道德违反。但也必须是这样:p构成了格赖斯 (Grice) 所说的S的「个人」理由[30]——即可以成为她愤怒的理由:一个理由,合理地说,S所知道的理由。[31]如果我不知道你背叛了我,但实际上你确实背叛了我,那么会存在一个我生气的理由,但我不会拥有一个生气的理由。[32]此外,S的愤怒还必须由她所拥有的理由适当激发,并且与该理由相称。假设我知道你对我撒谎,但我的愤怒是基于其他原因形成的:我只是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感到愤怒。或者,假设我发现你对我撒谎,说你喜欢我做的一顿饭,然后我因此陷入了狂暴且持续一生的愤怒。在这两种情况下,我的愤怒似乎都不恰当;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我的愤怒没有被我所拥有的理由适当激发,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我的愤怒与我的理由不相称。[33]
关于愤怒的进一步要求是,它必须针对与自己有适当个人联系的事情。那么,如果我对早期现代欧洲女性被作为女巫烧死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是否恰当呢?有些人可能会倾向于在愤怒的恰当性上加入某种接近性条件,而我的论点并不需要排除这种条件。(实际上,由于我这里的重点是受害者是否应该愤怒,我主要排除了那些「无关」的第三方愤怒但具有适得其反效果的情况。)但我要说的是,认为我们只能对在空间和时间上足够接近我们的事情,或与我们有特定个人联系的事情感到恰当的愤怒,这种想法可能会演变成一种令人不安的道德狭隘。确实,即使声称当自己社区的成员受到伤害时,自己有更多理由生气,或者有理由更加生气,这一说法的合理性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补充事实。我本能地被这样一种想法吸引:当一个年轻的黑人在街头被枪杀时,黑人美国人有特别的、额外的理由感到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黑人美国人喊出「我们的又一个孩子死了!」似乎是恰当的。但我并不太倾向于认为,当另一个中产阶级白人男子遭受伤害时,中产阶级白人男子有特别的、额外的理由感到愤怒。在这里,喊出「我们的一个人受害了!」似乎并不合适。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团结都是同样正义的,也不是所有形式的情感偏袒都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伯纳德·威廉斯 (Bernard Williams) 曾经有力地论证,当一个人面临救他的溺水妻子或一个陌生人的选择时,他不仅有理由救他的妻子,而且应该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仅仅因为「那是我的妻子!」 任何额外的、用来辩解的想法——例如「那是我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救自己的妻子是允许的」——在威廉斯看来,都将是「多此一举」。[34]这可能是真的。但对于那个愤怒地喊出「他是我们的人!」的富有的白人来说,他似乎有了完全错误的想法。/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beikaoshenguojiao.scieok.cn/post/4695.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对不义的愤怒总是恰当的吗?
76601 人参与 2024年07月23日 14:34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