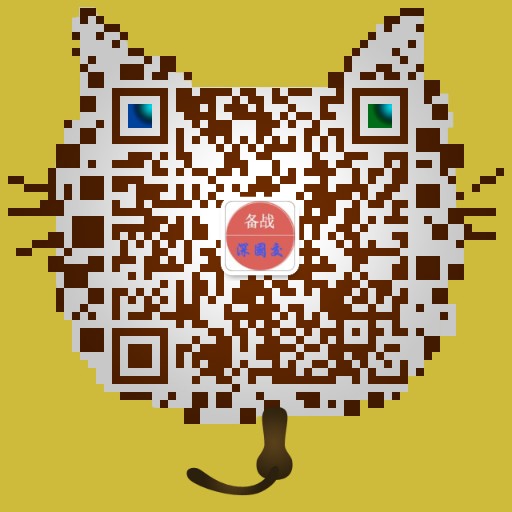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深国交哲学社 » 正文
-

女权主义和跨性别理论挑战性 (sex) 与性别 (gender) 这组「唯一的」二元系统,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可能会创造一组关于「颠覆性的跨性别」与「保守的跨性」的新的二元对立。本文旨在改变关于身体是真实的 (real),还是构造的 (constructed) / 可变的 (mutable) 这一议题的争论;并指出该争论建立了一个可以通过科学的重新评价性与性别而超越的错误二元对立。当下诸多生物学和神经科学都强调非线性 (nonlinearity)、偶然性 (contingency)、自行组织性 (self-organization)、以及开放性 (open-endedness) 的重要性。将这些研究纳入考量可以为当下无休止的理论僵局提供出路。
译注:原标题用词为“Bodily Becoming”。“Becoming”在此处除了变化本身外还特别强调了“成为”或“转变”的对象。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Bodily”的意思是“身体性的”,而非“身体的”,它修饰的是“Becoming”的过程且与同一过程中出现的其它类型的转变相互联系。
关于作者: 
翻译 / 理查,bananafish,fei
编辑 / CC
排版 / Luna
跨性 / 跨性别【1】(译注2)学者与大多数女权学者的研究都很少涉及生物学意义上身体【2】细节。虽然,正如我们在《跨性别研究读本》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Whittle 2006) 中所见的那样,生物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对立被视作女权主义和跨性 / 跨性别研究中争论的核心,这一重要的文集中却鲜有文章检验这个二元对立。然而,「酷儿/ 跨性别 (transgender)」和「跨性 (transsexual)」活动家之间明显的两级分化却很容易导致「颠覆性的跨性别」和「保守的跨性」间的身份对立 (Namaste 2000; Serano 2007)。这些情况让我们对具身性 (embodiment) 的地位——当跨性 / 跨性别和性别被我们同时理解为社会现象和物质现象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问题。 本文认为,当下观念的和政治的分界线与其说是在强调培育与天然的对立,不如说是在支持多样性而非二元论。通过鼓励「性别反叛者」对性别二元论的直接攻击,并同样接纳那些性别身份不被持续标记为「异类」的人(不论 Ta 们的自我认同是跨性、跨性别、性转,还是其他),我们才能重新创造「为所有性别 / 性别认同人群创造具有安全感的世界」的运动同盟 (Serano 2007, 358)。我们需克服性别观念,特别是跨性 / 跨性别中的二元对立:例如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以及颠覆性的性别认同和保守的性别认同之间的对立。关于身体是真实的 (real),还是构造的 (constructed) / 可变的 (mutable) 这一议题的争论预设了一个错误的二元前提。重新以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视角审视性与性别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它。 虽然关于性别发展中生物性因素角色的论断需要仔细的审视,但这些观点不应被拒斥,特别是当它们强调非线性 (nonlinearity)、偶然性 (contingency)、自行组织性 (self-organization)、开放性 (open-endedness)、以及成为 (becoming) 等概念时。对生物学的一种开放和有创造性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将性和性别的多样性视为连续的,而非二分的。(译注3)简单来说,「自然」提供了所有这些多样性,社会则需要接受它【3】。为了论述这一观点,本文会首先考察跨性 / 跨性别和女权主义研究中关于跨性 / 跨性别和性别二元性的争论;其次,本文将概述试图超越本质——建构二元论的女权主义方法;第三,本文将生物科学解读为「开放」,并有制造多样性的创造力的。最后,本文对最近的一篇关于跨性 / 跨性别原因的神经学文章进行了重新解读。

女权及跨性别争论 社会建构与社会化理论 (socialization theory) 是等同的么?女权主义分析通常认为,性别的生物学解释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中之外,且同时正当化男性的统治地位。因此,应该将重点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性别问题上。这一对生物决定论的拒斥有时导致任何对生物学意义上身体的讨论都被视为本质主义,这也就使许多女权研究者忽视生物学细节,放弃了生物学领域的研究 (Birke 2000, 29-34)。在1970年代中被热烈采用的性与性别的区分通常意味着作为社会产物的性别才被视作是「我们的」领域。实证主义的科学家往往错误的将社会建构主义分析等同于关于性别发展的社会化理论 (McKenna and Kessler 2000, 69) 。女权主义分析在不假思索地拒绝任何对性别的生物学分析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虽然近些年来经验性的证据并未支持社会化理论,但社会建构主义分析的重点旨在同时批判从男 / 女为唯一可行的性别划分出发的社会化理论和生物研究。 所有的人类知识——生物的以及社会的——都是由社会生产,并通过机构、政府政策和资金、学科限制与偏见、地方实践以及学校和实验的优先事项所组成的复杂网络而被文化接受并获得其有效性的。我们需要接触生物学解释,并将其纳入更广泛的社会框架来考虑;对于进步的女权主义或跨性 / 跨性别政治来说,生物学话语并不一定带来特别的威胁。生物决定论确实内含反动性,例如,纳粹试图消灭「作为次等人类的」同性恋者。然而,与异性恋霸权结合的社会化理论也是反动的——比如,对同性恋以及跨性 / 跨性别人群实施的性别纠正治疗,以及对双性婴儿进行的医疗干预。 
性别的模糊性 / 图源: Plus Diana Fuss 为反本质主义偏执所导致的僵局提供了一条出路,她提出:「所有的性别建构主义均依赖本质主义,因为男性与女性的这一分类需要最小程度的连续性和共性。」通过区分「利用」本质主义与「陷入」本质主义——即激进的运用与保守的运用 (Fuss 1989, 20)——她指出漠视这一区分会使我们过于坚持「本质主义永远呈现出反动的面目,就好像本质主义自身存在一种本质一样」(21)。如果摒弃「生物主义」,我们就会忘记那里确实存在需要通过研究什么是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以及这些类别如何在话语中发展和制约彼此来理论化的生物因素。二十年后,正如 TSR 中所示的跨性别研究那样,绝大部分的女权主义仍然看起来对接触生物学感到极度焦虑。在跨性 / 跨性别研究中关于病因学 (etiology) 是否重要,以及一个本质上具有性别的「我」的隐喻在跨性叙事中的意义的争论一直在进行。 关于性别背后的成因,特别是跨性 / 跨性别背后的成因真的重要么?还是说我们应当只是接受跨性别人群的存在与并与之相处?占据众多生物医学和社科类文献的病因学研究展现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范式丰富的失败史【4】。在跨性 / 跨性别政治中,许多人反对关注「为什么」跨性者存在;因为 Ta 们将这个做法视作一种不接受 (Serano 2007, 188) 或者是一种对「治疗」的寻求 (Devor 1997, 585)。的确,与其纠结于寻求跨性 / 跨性别者存在之正当性,我们更应接受 Ta 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事实,并研究 Ta 们「如何」与社会机构联系 (Namaste 2000, 55-56),并致力于创建包容性别多样性的社会 (Devor 1997, 586)。然而,跨性(transsexual) 群体经常运用「跨性是由不受家庭动态影响的不可观测的生物机制造成的」(434) 这样的声明,特别是当 Ta 们希望让家庭成员安心的时候。主张将性别认同障碍诊断从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删除的人通常使用一种神经学模型,Serano近期则提出使用「生物经验模型」来抵消社会和心理模型带来的负面影响 (Serano, 2008)。 我认为「为什么」这个问题确实事关紧要。原因如下:首先,跨性 / 跨性别人群认为这在 Ta 们的生活经历中很重要,尤其是在改变发生前后;其次,文化中常见的对基因决定论的痴迷问题必须得到我们的重视,而不应该被忽略。此外,生物话语有策略上的效用,特别是被用来挑战还原论的生物决定论的时候。有许多反对精神病治疗统治地位的抗争——例如,取消或改革对性别认知障碍症的诊断; 最后一个原因,在关于跨性者和跨性别者的类别和权利的「边界争议」中,病因学是至关重要的。 
Transpride Fist / 图源:Teepublic 跨性是保守的么?跨性别是具有颠覆性的么? 「跨性别」这一类别已迅速演变:70年代普林斯的跨性别主义为那些不愿意做身体改变的人提供了跨性的替代选择 (Ekins and King 2006, 13);Bornstein 的越界反身份认同旨在打破性别二元论 (Bornstein 1994);Feinberg 呼吁所有被二元性别排斥的人进行一场社会运动 (Feinberg 1996) 并以此定义一个研究领域 (Ekins and King 2006, 13-27)。一些学者担心,明确的跨性呼声可能会被跨性别的声音压制甚至抹去。将注意力集中在性别人造性上可能会淡化改变性别——身体的需要,而这却是跨性者最核心的生活经验。跨性别可能成为一种排他的身份——仅涉及那些寻求在公共身份中「打破性别二元性」的人 (Prosser 1998; Rubin 1998; Namaste 2000) ——而不予考虑酷儿 / 跨性 / 跨性别理论和社群中的跨性叙事。虽然 Rubin 建议「摈弃关于跨性主义或跨性是否明确具有颠覆性或霸权性的问题 (Rubin 2003, 184),二元性仍在相关讨论中挥之不去。许多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创造了一种二元对立,将跨性别叙事赋予颠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挑战性别二元对立的属性。与此同时,将跨性 (transsexual) 叙事贬低为保守的、本质主义生物决定论的墨守成规 (Rubin 1999, 177; Prosser 2006, 265)。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另一边,一些活动家(Ta 们可能自我认同为「跨性主义者」)试图通过生物学论点来支持「生在错误的身体」的这一传统的跨性叙述,明确排斥跨性别 (transgender) 的表达,并时常标榜「跨性生活的人群……实际上强化了性别的二元概念」(Gurney 2004, 344)。跨性被塑造成是生物性的、内在的,而不是选择的,因此应该得到社会和法律体系的承认;而跨性别被认为是社会的、习得的、自由选择的,因此不应该得到法律上的性别更改,只可得到法律对其免遭歧视的保护 (Wallbank 2004)。作为比较极端的情况,一位支持用「哈里·本杰明综合症」取代跨性主义的人表示,「所有患有哈里·本杰明综合症的人都应该坚决与‘跨性别者’保持距离」,因为跨性别者正试图「利用 Ta 们与哈里·本杰明综合症连系来获得同情」(Goiar 2008) 【5】。一个相对具有更多包容性的模型则将生物学和社会学视作相互交织的。这种观点认为生物和社会的交织作用体现在所有形式的性、性别、性别表达和身份中,并力图为所有性别立场建立合法的政治联盟以获得法律和社会承认。我们需要的是批判性的社会理论来为性别多样的人群建立社会运动,而不是仅限于在学术界内对社会理论的有限参与(Namaste 2000, 28-30)。我们需要一个置身于日常社会世界的社会关系背景下的反身性的,而非客观性的研究框架,以解释跨性 / 跨性别者如何看待 Ta 们的生活和经历。虽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我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是「向上研究」那些研究跨性别的人,而不是「向下研究」边缘化的跨性别者群体。这项研究指向发展一个新的概念框架的重要性,它可以取代旧的二分法,并更有效地理论化性 / 性别化的身体【6】。 
超越本质主义和建构,转向身体的成为 (The Body Becoming)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和其他社会分析都极其有效。利用「性别」来指示生物学上的性进入社会讨论领域有利于去自然化性别差异;女性的生理构造不再能把她们贬低为卑躬屈膝之人。然而,这种性 / 性别之区分越来越遭到质疑。其核心问题是,性、生物学以及自然通常被视为固定不变的:它们是社会书写的底板。相反,性别、社会和文化被视为变化和动态的领域——所有重要的事都在这一维度上发生。这就导致生物性的角色被最小化——只被描绘成(对可能性的)限制而不具备潜力。许多女权主义研究从性别的角度动摇性 / 性别的划分。它们提出:我们重视性别差异仅因为我们从异性恋规范性的假设之上出发。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中,生物(或其他「自然的」)物质性可以被认为是话语的效果,不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跨性 / 跨性别研究同样回避与生物学的交集,这呈现了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女权主义者对颠覆性跨性别理论的强大影响,并反映在对跨性群体渴望通过身体改变获得真实性的本质主义指控中。考虑到激素对跨性别者身体和行为的复杂影响,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通过同时支持并否认了霸权式的对激素和行为的影响,它让异性规范性 (heteronormativity) 和酷儿都出现了混淆 (Rubin 2003, 152-60; Serano 2007, 6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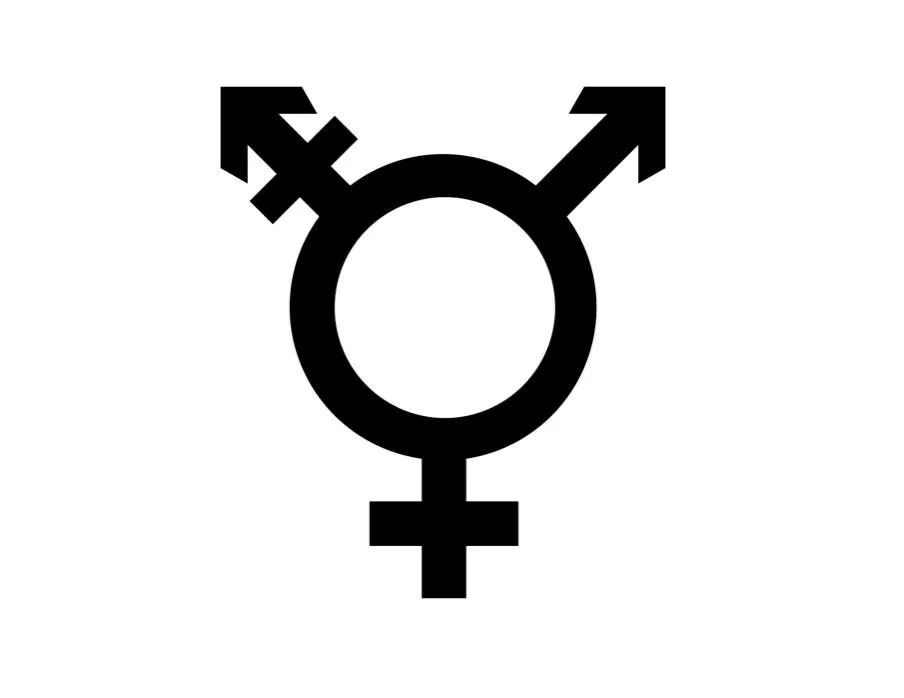
Transgender Logo / 图源:Wikipedia 在试图解决「身体」问题时,Butler 和 Grosz 探索了相反的方向—— Butler 对异性规范性的建构能力的关注指出了性「总是已经是性别」(Butler 1999, 11),而Grosz 对不可划约的性差异的关注则抛弃了性别,而倾向于性。然而,我认为保留性和性别作为不同的分析范畴可以让我们在不将跨性者的生活经历视为「虚假意识」的情况下,将跨性理解为社会建构的。同时,这也避免了因忽视「跨性者叙事的决定张力」所带来的危险 (Rubin 2003, 18)。 由于社会建构主义者对文化实践的关注可能会忽视生活中的身体,将性化的身体视为被动的生物基质 (Birke 2000, 34), 理论界需寻求新的理论方向。Butler 的分析集中在语言话语中性化身体的物质化,并限于在文化上可理解 (culturally intelligible) 的身体表面 (Cheah 1996)。在自然 / 文化二元论的两方面互为限制的同时,Butler 仍然强调了性的生物物质性的固定性,和性别的灵活性 (Roberts 2000)。身体的物质性以及它们是如何在生活经验中发展仍然是不可见和不可理解的,并仅限于生物学家的研究之中。Grosz 在 Volatile Bodies (1994) 一书中更深入地研究了生物学的细节,讨论了生活体验和性身体的「躯体流动 (corporal flows) 。她的论断「从广义上说,文化、历史和语言的存在必须在于人类生物学的本质中」(Grosz in Wilson 1999, 7),对任何一个有生物学背景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从一个在后结构主义传统中的女性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却似乎令人吃惊。它设想了一种肉体上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与生物学上的解释深深交织在一起」(Wilson 1999, 8)。Grosz 否认物质身体及其表征是相互分离的 (Grosz 1994, x-xi),并指出了文化和物质 / 自然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然而,她强调的依然是文化差异的策略价值,而不是身体物质性的相对固定性。生物因素主要被理论化为对社会因素的约束,而非相反。这使得消极的生理与积极的社会之分裂再次出现。然而,理论化自然和文化的内在牵连使重点从「身体是生物还是建构的」移开,转向对「对身体的审视如何证明这些范畴的局限性」的探讨 (Roberts 2000)。为了掌握生物性的身体,女权主义的分析需要从身体作为约束性的、固定的和天生的观点转向「身体的成为」作为一个动态、变革性过程的立场。格罗茨最近的工作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下面的另一部分将对此进行概述 (Grosz 2004, 2005)。 
Volatile Bodies 封面 / 图源:Routledge 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结合了将科学视为人类文化活动的理解,以及关于科学研究对象所引发的问题的理解。Haraway 既反对实证主义科学的客观主义,也反对科学描绘成众多修辞故事之一的强建构主义的相对主义观点 (Haraway 1991, 183-202)。相对主义之问题在于,参与政治的人需要更可靠的对世界的描述来挑战统治关系。当女权主义者和其他科学批评人士寻求强大的工具以「解构敌对的科学真理主张 (truth claims)」时,Ta 们最后接受了「认识论休克疗法」,以「自我诱发多重人格障碍」收场 (186)。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同时叙述极端的历史偶然性以及通往理想的‘真实’世界切实可行的承诺」(187)。Haraway 提出的一种思考路径是通过一种「情境化的认识」来理解客观现象,也即是说其得出的观点总是源于其所处的情境视角。这样一来,要认识客观世界就必须视客观事物为行动者或主体了。事实上,自然 / 世界或生物学存在并非被动地受文化语境摆布。自然 / 世界 / 生物学因素实际上是能动 (active) 的,尽管它们的行为规律与人类不同。这使得我们「永远质疑诸如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尽管不排除其策略效益」(199)。无论是从生物决定论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文化构建论的角度,人体这一概念其实都并未被完全理解。尽管人们没法跳脱出语言或词句来理解人体,但人体也不(完全)是语言构造的。 Haraway、Grosz 以及其他学者 (Barad 1996) 和女性主义生物学家 (Spanier 1995; Fausto-Sterling 2000) 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策略。它允许我们通过理解生物和社会因素的互相作用和同时的主体性,削弱自然与文化、本质与建构之间二元对立。在这种语境下,生物意义上的人体不再被动地受到话语的构建,它反而向话语施加了作用。我们也因此有了从大脑和身体层面上研究性别差异,以及这种区别是如何作用在非常规性别者 (gender variant people) 身上的工具。从生物和心理学的研究上看,对荷尔蒙和动物行为关系的研究结论在人类身上往往被过于直接地套用 (Fausto-Sterling 2000, 232)。通过研究性别差异在行为和认知上的体现,小的平均差异往往被解读为男性和女性具有本质上不同的大脑类型。像是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这样的学科如今已因为其理念中的本体论还原主义被广泛批判,其过分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以及基因决定论被视作对男权统制的洗白与辩护(Roughgarden 2004, 172-75)。(与此相对,Haraway、Grosz等人的)这个倾向的一个关键理解是:「生物学是与其背景环境不可分割的,自然或先天是不能和后天分开的」(Spanior 1995, 19) 。 社会生物学的可加模型忽略了对象发展与成长过程中不可计量,不断累积的交互活动。而这些二元论的观点则会同时在自然与文化这两个方面取消它们的对立:首先,它指出进化过程和自然本身是极富多样性和动态性的,而人类社会与文化却是相当程度上僵化且固定的;其次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动物也可以拥有社会文化;其三,在动物界极其多元的性存在和性别表现面前,人类的复杂表述反而失去了特殊性。女性主义和跨性 / 跨性别研究都应当接纳这种新的,非线性的生物学,并且意识到这对于进步主义运用的潜力。尽管如此,女权主义者需要真的做到这件事情却不容易 (Keane and Rosengarten 2002)。 Butler 的论文「给人以公正」(2006) 就展示了我们与生物话语接触时可能犯的错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大卫·瑞米尔 (David Reimer),由于一场拙劣的割礼而被迫转性为女孩的男生。Butler 批判 Money(译注4)利用了这场悲剧来为性心理的天生中性论提供支撑 (Butler 2006)。而 Diamond(译注5)则用大卫排斥女性身份的事实来证明性别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因素 (Butler 2006, 186-86)。然而,Butler 误认为 Diamond 只是在提倡人们将带有 XY 染色体和一个小到甚至不存在的阴茎的儿童视作男性,并仍然支持手术干涉。这实在是莫大的误会,因为在中性幼儿问题上,Diamond 实际上是著名的反干预者【7】。Butler 似乎受到了学科视角的束缚,仅仅引用了两篇生物学的论文:Diamond 和 Sigmundson 的访问调查报告 (Diamond and Sigmundson 1997b) 以及 Fausto-Sterling 的一篇专著(Fausto-Sterling 2000, 45-77)。何况 Fausto-Sterling 也指出,Diamond 提出的新型治疗范式首先就是要搁置粗暴直接且不可逆转的手术疗法 (70)。 
David Reimer / 图源:Mobidology 这个误读严重吗?实际上这并不影响 Butler 的核心论点:认为大卫·瑞米尔的经历不能为性别的社会决定论或生物决定论提供例证。相反,她认识到这一故事提供了一种充满前途且令人惊喜的、被爱的可能性,唤醒超越了生理机制和性别规范的「自我」(Butler 2006, 191-93)。无论如何,大卫·瑞米尔的悲剧如今已经因为性别的先天后天之争而变得传说化了。由于巴特勒在酷儿以及跨性 / 跨性别研究上极大的影响力,以及这是唯一一篇在《跨性别研究读本》(TSR) 上讨论大卫·瑞米尔问题的文章,许多读者可能将这种观点视为一种权威的解读,因而将 Diamond 视作一个保守的生物决定论者【8】。而 Diamond 实际上是非典型性别群体的重要政治盟友,他明确地反对将间性、跨性别和跨性视为疾病,并且宣称 Ta 们代表了健康的多元性 (Diamond 2005)【9】。这一错误还妨碍了 Butler 论点中重要的一部分,即对于曼尼而言,阳具的存在是男性的重要标志,而对于 Diamond 而言,则是Y 染色体。她指明了一条理解社会建构和基因影响的全新路径,而不是重复「自然和规范性别的供应商们」提供的路径 (Butler 2006, 188)。的确,Diamond 本人是批判二元性别规范的。他将社会性别,生物性别和性别取向这一整个范畴的表达视为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自然」产物。因此人们应有权以任何其乐意的性别自居 (Diamond 2006)【10】。 (待续,后文将会讨论如何将生物学基础与创造多样性结合起来) 译注: 1.原标题用词为“Bodily Becoming”。“Becoming”在此处除了变化本身外还特别强调了“成为”或“转变”的对象。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Bodily”的意思是“身体性的”,而非“身体的”,它修饰的是“Becoming”的过程且与同一过程中出现的其它类型的转变相互联系。 2.本文作者区分使用了trans/transsexual/transgender,译者根据作者意图将trans翻译为“跨性/跨性别”,transsexual翻译为“跨性”,transgender翻译为“跨性别”。详细情况请见原作者注1。 3.可以参考Fausto-Sterling, A. (1993). “The FiveSexes.” 和Padawer,R. (2016). “The Humiliating Practice of Sex-Testing Female Athletes.” 4.约翰·曼尼(John Money),新西兰心理学家.大卫·瑞米尔性别重置手术的主治医师,提出性别认同具有可塑性,在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了性别认同诊所。大卫·瑞米尔正是在该诊所完成的性别重置手术。 5.弥尔顿·戴蒙(Milton Diamond)对大卫·瑞米尔于1993年作了后续的访问调查,于1997年3月在《儿科及青少年医学汇刊》(Archives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发表。 原注: 【1】「跨性 / 跨性别男性」 (trans man) 指代一个生在女性身体的作为男性生活的人。这些术语的意思是有争议,且经常在不同人那里有不同的意思。一些认同为「跨性别」的人经历了身体改变,而一些认同为「跨性主义者」(Stone, 1991) 则拒绝身体改变(以及 passing)。 【2】一些例外包括女性主义生物学家 Rogers (1999), Fausto-Sterling (2000), 女性主义科学研究者 Bleier (1984), Wijnggard (1997), Hird (2004), Wilson (2004), 以及对生育的讨论 (O’Brien 1981)。 【3】这篇文章中的论点符合新的经验研究和博士论文,虽然由于时间较早,本文中的采访数据较少。 【4】关于产妇影响 (Stoller 1996)、循环激素水平、 H-Y 抗原和LH反馈机制的理论都被随后的证据所推翻 (Gooren 2006)。 【5】Rachael Wallbank 比哈里本杰明综合症活动家要细致 (nuanced) 得多(具体内容过长且不重要,在此略过)。 【6】我将在2009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会检验政治和社会对于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这些知识主要关于跨性 / 跨性别的生物基础。我的论文会包括对生物学、神经学、心理学和社会研究者,以及临床医生和跨性 / 跨性别活动家。 【7】Butler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两个1997年3月的文章,其中一个来自纽约时报 (Angier 1997),另外一个来自 Diamond 和 Sigmundson,它们看起来能够支持 Butler 的论点,但实际上是错误解读。(细节较多且不重要,在此略过)。 【8】Butler 修改了她 2001年的文章并收入了《消解性别》 (Undoing Gender, 2004) 中,但她没有修改对于 Diamond 的描述。类似的,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TSR) 可以补充一个修正性的脚注,但最终只是重印了原文章。 【9】在我的眼中,Butler 和 Diamond 只有比较不重要的关于现实问题的意见差别,涉及的问题包括法律上的性别更改、将 GID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从 DSM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中去除、医疗保险、组织反恐跨活动等。 【10】一则支持作者对 Diamond 评价的语录,Diamond 在此维护了跨性别女性。(细节过长且不重要,略)。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 哲学社
推荐阅读:
版权声明:“备战深国交网”除发布相关深国交原创文章内容外,致力于分享国际生优秀学习干货文章。如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原谅,并联系微信547840900(备战深国交)进行处理。另外,备考深国交,了解深国交及计划参与深国交项目合作均可添加QQ/微信:547840900(加好友时请标明身份否则极有可能加不上),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
非常欢迎品牌的推广以及战略合作,请将您的合作方案发邮件至v@scieok.cn本文链接:http://beikaoshenguojiao.scieok.cn/post/2410.html
-
<< 上一篇 下一篇 >>
跨性 / 跨性别,一种身体性的成为:重新思考多样而非二分的生物性(上)
27385 人参与 2021年10月09日 17:26 分类 : 深国交哲学社 评论
search zhannei
深国交2024年英美本科录取小计
-

未标注”原创“的文章均转载自于网络上公开信息,原创不易,转载请标明出处
深国交备考 |
如何备考深国交 |
深国交考试 |
深国交培训机构 |
备战深国交 |
联系方式
Copyright www.ScieOk.cn Some Rights Reserved.网站备案号:京ICP备19023092号-1商务合作
友情链接:X-Rights.org |中国校园反性骚扰组织 | 留学百词斩 | 南非好望角芦荟胶 | 云南教师招聘考试网 | 备战韦尔斯利网| 备战Wellesley